
点击右上角![]() 微信好友
微信好友
 朋友圈
朋友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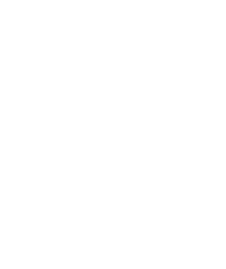
请使用浏览器分享功能进行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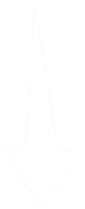
作者:杨再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贵州发展制度保障高端智库副教授)
今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25年贵州考察时提出“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的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构建内需驱动型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遵循。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从外需依赖向内需主导转型的关键阶段,亟需从理论层面突破传统需求管理范式,探索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制度创新与治理效能协同演进的内生动力机制。
供给创新与需求扩容的辩证统一
传统需求管理理论将内需不足归因于有效需求疲软,主张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消费,但这一范式难以解释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大背景下消费升级的结构性矛盾。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已超4亿,他们不是没消费能力,而是普通商品满足不了其升级需求。比如,老式家电再便宜也难激发购买欲,但智能家电哪怕价格高仍受青睐,这说明单纯刺激消费治标不治本。就像手机市场,功能机折扣也卖不过全面屏,因为消费者要的不是便宜货,而是能刷短视频、玩云游戏的新体验。供给侧创新能够突破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固有规律,其理论内核在于“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适配机制。即当供给端通过技术革新、场景重构或价值嵌入实现产品迭代时,消费者潜在支付意愿将随之被激活,形成需求扩容的乘数效应。从政治经济角度看,供给创新是生产力和消费力运动的结果。数字时代,大数据改变了生产方式,让供给从“功能型”变成了“共创型”。例如,文旅资源转化成数字资源后,就能给消费者带来更多沉浸式的体验。基于此,消费者对文化产品的想法发生改变,通过互动形成关于需求的价值认同。这种“供应变需求”的关系,证明了马克思的“生产直接是消费”的观点。
城乡融合与内需双循环的协同演进
城乡二元结构对消费潜能的抑制,本质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滞后引发的制度性梗阻,让内需始终“跛脚走路”。比如,农民想进城打工却落不了户,城里企业想投资乡村又怕土地权属不清,结果就是农村资源闲置、城市产业单一。要激活内需,得先拆掉“三堵墙”:第一堵是“土地墙”,让宅基地、承包地能抵押能流转,农民有了“活资产”,才敢贷款创业、进城买房;第二堵是“数字墙”,只有5G基站、物流网络进村,城里人才能网购山货,村里人也能享受远程医疗,消费场景自然打开;第三堵是“身份墙”,农民工市民化后,教育医疗支出会催生新消费。值得注意的是,城乡融合不仅是地理空间的整合,更是社会关系的重构。政府通过公共品供给优化消费环境,市场通过供应链下沉拓展服务半径,社会通过组织创新培育消费共同体,形成“制度供给—市场响应—社会参与”的协同机制。当城乡要素像活水般自由流动,农民钱包鼓了,企业订单多了,内需大循环自然转得动。
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动态平衡
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交易成本对市场活力的决定性作用,但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制度创新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共生现象。比如优化营商环境,不是政府当甩手掌柜,而是当好“制度设计师”,建设消费争议平台,让消费者在手机上简单操作就能解决纠纷,实现了“降成本”和“提效率”的双赢。这种“制度集成创新”模式,为新兴经济体破解“制度性交易成本困局”提供范式参考。更深层的理论贡献在于,中国制度创新始终以“发展型治理”为导向——党建引领就像黏合剂,把政府、企业、社区拧成一股绳;政策试点不是瞎折腾,而是小步快跑试错,有了好经验再全国推广;数字技术则是制度落地的加速器,比如用大数据抓取企业需求,政策补贴自动到账,省去层层审批。通过党建引领整合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政策试点构建适应性学习机制、通过数字技术重塑制度执行效能,形成“制度创新—治理升级—发展跃迁”的正反馈回路,这种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再内化为发展动能的实践逻辑,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新的理论增长点。
消费升级与社会再生产的系统耦合
内需驱动机制的本质是消费升级与社会再生产的系统耦合。当消费结构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时,对产业升级的反向牵引力显著增强。比如,老年人青睐生态康养,养老院就得装智能监测设备、开发药膳食谱;年轻人追捧非遗文创,手工作坊就要学会3D建模、直播带货。消费者不再是被动选择,而是通过体验反馈成为“产品经理”,这种“需求侧价值偏好—供给侧技术路线”的互动关系,让消费端与创新端真正“手拉手”,推动社会再生产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转型。内需不再是经济运行的终点,而是产业升级的新起点,实现消费与创新的深度融合。
内需驱动机制的理论重构,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范式从“外源性增长”向“内生性发展”的深刻转变。构建“供给创新激活需求—制度创新畅通循环—治理创新保障效能”的动态模型,需突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窠臼,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整合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社会治理的多维视角。未来研究应进一步关注数字技术对消费关系的革命性影响、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分配制度创新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全球化溢出效应,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工具。
